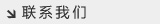经合组织(OECD)在首次发表的中国经济调研报告中预测,2010年,中国将超过美国和德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国。与此同时,中美、中欧贸易摩擦有加剧的趋势,国际上批评中国奉行重商主义信条的言论也与日俱增。
重商主义盛行于十六、十七和十八世纪的欧洲,认为国际社会处于一种彼此争夺权力与财富的无政府状态,国家间关系是一种"零和"博弈,一个国家的获得就是别的国家的损失,一个国家要改变或改善自己的国际地位,就只有掠夺别国的财富。重商主义者声称,衡量一个国家是否在经济上取得成功,应该看它黄金储备有多少,而增加黄金储备的办法是鼓励出口、限制进口。重商主义的基本信条是:1、排斥(价格)竞争;2、国家应干预经济活动;3、以累积黄金白银为主要目标,即追求贸易顺差。斯密在1776年发表的《国富论》中把重商主义者驳斥得体无完肤,他的观点非常鲜明:放开市场和贸易是"好事"而不是"坏事"。尽管如此,仍止不住重商主义以各种面目重新出现于国家的政策之中,成为当前推行贸易保护主义、阻碍全球贸易自由化的重要因素。现代版的重商主义将对外贸易作为刺激国内经济的工具,出口盈余及相应的货币存量的增加是关键性的手段,并以充分就业作为最主要的行动目标。现代贸易摩擦的关键就在于出口国低价商品对进口国同类商品行业冲击后所引发的较为严重的失业问题。引起中美、中欧之间贸易摩擦的关节点即在于此。
毫无疑问,重商主义也曾经影响过中国的经济政策。从贸易政策来看,长期以来中国奉行的是以"出口创汇"为基本原则的传统贸易战略。为了扩大出口创汇,政府采取了一系列鼓励出口的优惠政策,如为出口企业提供优惠贷款、贴息、出口补贴、退税等,这些措施的实施使得中国外贸出口连续20多年保持高于GDP增速一倍的速度增长。然而这种具有强烈"重商主义"色彩的贸易增长方式带来的负面影响也不可避免:首先,鼓励出口的优惠政策扭曲了国内经济的资源配置,也加重了政府的财政负担;其次,持续的贸易顺差导致中国外汇储备规模急剧扩大,对人民币汇率的稳定和中国经济发展造成不利的影响,而贸易摩擦增多则是中国传统贸易战略的必然结果。
当然,采取具有"重商主义"色彩的出口导向政策,也是改革开放之初一种迫不得已的选择。当时国内消费市场狭窄,居民购买力不高,只能采取以国外消费替代国内消费的策略。但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国内消费市场不断深化,居民购买力大幅提升,充分挖掘国内市场应是我们的着力点。
经济学理论告诉我们,贸易逆差长期存在的根本原因在于国内储蓄不足,巨额贸易顺差则在于国内储蓄过度。根据世界银行最近公布的全球穷富报告显示,中国内地的真实储蓄率为25.5%,排名仅次于海地而居世界第二,而美国的国内真实储蓄率仅为8.2%。现在我们指责美国一味向外而不是向内寻找贸易逆差原因已无意义,重要的是如何使国内居民高居不下的储蓄率降下来,即如何提升居民消费水平。这就要求我们将以出口导向为主的经济政策向内转,转向以扩大内需为主的经济政策。假设中国断绝了外贸和外资,其经济增长率只会下降1%至2%,对于一个以9%以上速度增长的经济体来说不足挂齿。这当然并不是说不重视对外贸易,而是说要对中国的外贸发展战略和现行外贸政策进行反思和重新定位。必须彻底改变传统的以出口创汇为首要目标、以牺牲国内居民福利为代价的粗放式外贸发展战略;必须彻底摒弃"重商主义"的片面追求增加贸易顺差的思想观念,实现进出口贸易基本平衡或略有盈余。与此同时,真正从制度上、政策上采取措施,将近年颇热的口号"扩大内需"落到实处。
如何扩大内需,是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必须解决的问题。其实,政府也早就认识到,经济增长最终必须走上主要依靠国内消费来推动的道路,仅仅依靠出口、外商投资和政府支出是不够的。
扩大内需是降低储蓄率的另一种说法,我国奇高的储蓄率之所以存在,原因不外乎两个:一是中国缺乏社会保障和养老金体系引发的预防性储蓄所致,二是中国缺乏合理的投资渠道,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很不完善。扩大内需亦须从这两方面入手,才能牵住牛鼻子。内需扩大了,就业率也就有保障了,过大的贸易顺差问题也会有很好的缓解。而达到这一切,都需要摈弃或明或暗的重商主义经济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