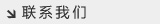目前针对此次危机爆发的原因有诸多研究,但研究范畴主要集中在微观层面,可以主要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金融产品尤其是衍生品的交易很疯狂。如果仅是如此,那么,美国正在对CDS市场进行整顿,是否就能解决问题呢?似乎不是这样。
二是金融机构尤其是投资银行的贪婪,以至于杠杆率过高。但从雷曼、美林、高盛这些金融机构的财务报表中可以发现,10年前亚洲金融危机时,它们的杠杆率同样非常高,为何那时的高杠杆没有导致投资银行的总体性崩溃?
三是金融监管缺失。每一次金融危机事后都可以看出金融监管在某些方面出现了问题,用事后发现的金融监管缺失难以圆满解释这次危机。
如此看来,将问题归结为这三个方面,难以让人完全信服。
当我们主要从微观层面讨论这次危机爆发的背景和原因时,美国人却主要在从宏观层面上进行总结。他们的一个基本结论是,这次危机的直接原因是美国居民的低储蓄率、高杠杆率。
有很多人将美国的低储蓄率归结为美国人的过度消费,因此认为美国的过度消费是导致次贷危机的根本原因。对此,美国人却有自己的辩解。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在国会听证时提到,危机肇因不是美国的过度消费,而是中国的过度储蓄,导致美国的流动性过剩,是中国的储蓄输出“挤出”了美国的储蓄,最终酿就这次金融危机。
事实是否如此?以下几个事实可供度量。
全球前四大经济体中,美国的储蓄率是最低的,低于日本、德国,更低于中国。只有美国的经常项目是长期赤字,其他三大经济体都是长期顺差,也就是说,只有美国在吸收和占用别国的储蓄,用它的消费推动全球的经济增长。
值得关注的现象是美国居民部门储蓄率的趋势性下降。1929年-2004年美国居民的储蓄率情况显示,除了1929年大萧条后的异常下降和1941年到1946年的异常上升之外,在1947年到1984年长达37年的时间里,美国居民储蓄率都维持在7%到11%左右。但是,从1984年开始,美国居民储蓄率呈现出一种趋势性下降的态势。从1992年开始,甚至储蓄额也开始下降。这种现象早于中国的储蓄输出——要到10年之后的1994年,人民币汇率并轨,中国出口产业才开始崛起。这意味着,美国居民储蓄率的趋势性下降发生在中国出口导向经济发展格局形成之前,而不是之后。因此,其较低的居民储蓄率不能简单归咎于中国。
财富效应与信贷便利性导致美国人过度消费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美国居民储蓄率的下降呢?美国经济学界目前已有大量的文献以此作为主题,总结下来大致有以下几种解释。
第一,统计错误。主要发生在两个方面:一是错误地将储蓄算成了消费,例如,购买电脑等耐用消费品,应该是投资(储蓄),而不是消费。二是少计算了收入,多计算了消费和消费税收,例如,美国居民的私人养老保险占整个养老保险体系的90%以上,在保险到期或分红时,居民会得到现金,这些现金在美国的国民收入账户里不统计为收入,但居民拿到这些现金消费时则统计为消费,并且要缴纳消费税,这就致使低估了收入、高估了消费,导致储蓄率的统计错误。据研究,这个问题存在,但并不重要。
第二,其他部门储蓄的“挤出”效应。但是,除1998~2001年,政府部门的储蓄率均为负数;企业部门虽然有储蓄,但没有出现储蓄率的系统性上升。因此,这一假设已经被排除。
第三,人口年龄结构老化。二战后婴儿潮在1990年代后期进入退休年龄,消费增加。这一假设也不成立,因为老龄化更加严重的日本和欧洲都有较高的储蓄率。例如,日本和德国的储蓄率是美国的2到3倍。
第四,财富效应。财富增长刺激了消费,降低了储蓄率。
第五,信贷便利性。信贷便利性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信贷的成本比较低,二是较为容易地获得信贷。
在上述几种解释中,我认为财富效应和信贷便利性是解释美国低储蓄率,尤其是储蓄率自1984年呈趋势性下降的关键原因。
财富效应没有反映到储蓄率的计算中,这涉及到两种不同类型的储蓄计算公式。
储蓄计算公式1(以家庭资产负债表计算):储蓄=工资+(资产增值+资本利得)—税收—消费
储蓄计算公式2(以国民储蓄账户计算):储蓄=工资+资本利得—税收—消费
家庭资产负债表和国民统计账户关于财富定义的差异在于:在家庭资产负债表中,资产(金融资产、房产)增值是财富;但是从国民收入账户来看,这不是“财富”,因为它不是可以用于新投资项目的可贷资金(loanable fund)。由于这点差异,财富效应没有反映在国民收入账户里面。
但是,仅仅用财富效应还难以解释1980年代以来美国居民储蓄率的系统性下降。财富效应自1946年以来一直存在,而储蓄率的系统性下降始于1984年。
所以,我们不可能用财富效应完全解释美国储蓄率的系统性下降,能够起到补充作用的关键因素是信贷的便利性。
信贷便利性首先体现为负债成本的趋势性下降。美国居民利息支出与其全部金融负债之比(即综合负债成本)由1984年的3.9%持续下降,至2006年仅为1.75%,呈现趋势性下降。同时,在综合负债成本趋势性下降的过程中,储蓄率也在下降,两者非常契合。也就是说,既然美国居民可以以比较低廉的成本借到钱,就不用在当期的可支配收入里留存更多的储蓄。
信贷便利性还体现为可以较为容易地获得信贷。美国的信贷可得性呈现趋势性的提高,其中一个非常关键的指标是信用市场工具。在美联储的资金流量统计里,信用市场工具指的是除股票和共同基金之外的所有金融工具,几乎涵盖了所有类型的债务资产,包括贷款、证券化产品、债券、货币市场工具等。美国居民的负债占全部负债(信用市场工具)的比重由1984年的33%持续上升到2006年的52%。信贷可得性的系统性上升与美国居民储蓄率的趋势性下降契合得非常好。
有了财富效应和信贷的便利性,就可以综合解释美国储蓄率的系统性下降。对此,我们做了一个简单的计量检验:用净值(即美国居民资产负债表的净值)、信贷可得性和负债成本作为自变量,储蓄率作为因变量。我们发现这三个因素可以解释83%的储蓄率变动。
由于储蓄和可支配收入相关,如果将可支配收入的增长速度加进去,这四个变量就可以解释91%的储蓄率变动。
由此可见,美国的储蓄率自1984年呈系统性下降之谜,完全可以用美国本身的经济金融指标予以解释,而不需要借助于中国的高储蓄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