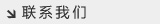全球经济失衡,孰之过
全球经济失衡并非一个新鲜词汇。2002年IMF提出了外部失衡(External Imbalances)的概念,2005年IMF总裁在一次演讲中正式使用了“全球经济失衡”(Global Imbalances)这个词汇,并且说道,不要相互指责。美国不要指责中国,中国也不要指责美国。全球经济失衡有两个表现:第一,美国持续并不断扩大的贸易逆差,以及包括中国、日本和德国在内的其他主要经济体的贸易顺差;第二,由于贸易差额反映了各国国内储蓄与投资之间的关系,全球经济失衡又表现为美国持续并不断扩大的储蓄缺口(储蓄率小于投资率),以及其他主要经济体的储蓄盈余(储蓄率大于投资率)。
对于全球经济失衡,过去的分析基本都是站在作为贸易逆差国和储蓄缺口国的美国的立场,其矛头所向是贸易顺差国的汇率问题和储蓄盈余国的高储蓄率问题。只不过为了抓住典型、以儆效尤,通常是以一个国家作为重点指责的对象,如上个世纪80年代的日本,90年代末期以后的中国。可是,如果换一个角度,从贸易顺差国和储蓄盈余国的角度看,讨论全球经济失衡自然应该从美国的低储蓄率和由此产生的巨额贸易逆差问题上着手。
美国消费型经济的两大成因
这里,需要注意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就是美国居民储蓄率的系统性下降——自上个世纪80年代的10%持续下降到2007年的接近于0。对于这种现象,美国学者以及我们从许多方面进行了分析,最终发现导致美国居民储蓄率下降的两个关键因素:资产价格上涨带来的财富效应和以按揭贷款为主的便利的债务融资。而这两个因素又同美国在上个世纪80年代推动的一系列金融改革有着密切的关系。
在经历了两次石油危机的重创之后,里根政府开始接受“供应学派”的改革思想。“供应学派”的改革方案包括减税在内的一系列具体措施,但其核心精神是放松过度的政府管制,推动市场化进程。这种精神体现在金融领域就是放松金融管制、推动金融创新。事实上,就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美国金融体系而言,其基本架构是在那时搭建起来的。例如,包括养老基金、共同基金在内的机构投资者,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纳斯达克股票市场、垃圾债券市场,有利于居民借贷消费的消费信贷和资产证券化产品,以及完全市场化的利率体系等等。
上世纪80年代美国的金融改革创造了有利于中小企业尤其是高新技术企业发展的环境,从而为信息技术革命奠定了基础,同时也推动了美国居民储蓄率的下降、消费率的上升。一方面,在居民持有的金融资产中,越来越多的是直接或者通过养老基金、共同基金间接持有的股票,股价的上升降低了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和养老储蓄;另一方面,在资本市场的竞争压力下,80年代后美国的银行业越来越多地发展居民贷款业务。现在,居民贷款已经占到美国银行业贷款的近70%。这样,就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资产价格上涨、居民贷款增加、储蓄率下降、消费率提高和消费主导的经济增长。
上世纪80年代的美国金融改革在国际上还产生了一个效应,就是美元的国际地位不断提高,并最终再次成为国际货币体系中居于垄断地位的货币。在上个世纪70年代,随着美元与黄金挂钩、其他国家货币与美元挂钩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美元的国际地位日渐衰落,而日元、德国马克、瑞士法郎等货币开始崛起,国际货币体系开始进入群雄争霸的多元储备货币体系时代——这种格局恰恰是我们今天所诉求的。然而,这样的格局并未维持很久。原因有很多方面,其中最重要的一方面就是像日本这样的经济强国并没有像美国那样去放松管制、推动金融改革。例如,日本直到1985年才允许发行无担保的公司债券,到1988年才允许发行商业票据,直到1994年才完成利率市场化改革,而一个以资本市场为基础的养老保障体系到今天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
显然,这里我们需要解释这么一个问题: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之后,为什么金融改革与否会决定各国货币国际地位的强弱?这是因为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标志着国际货币体系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信用本位制时代。在信用本位制下,各国发行的货币——包括中央银行发行的基础货币和通过商业金融机构创造的派生货币——都完完全全是以“信用”为支撑,而所谓的“信用”就对应着居民、企业和政府的债务。在信用本位制下,对国际储备货币的要求是:第一,要能够灵活自如地在国内创造信用;第二,要建立一个输出信用货币并使之再次回流的机制。要满足这两个条件,就必须拥有一个没有金融管制、金融创新频繁、资本市场发达的金融体系。
美国资产泡沫扩大的根源
美国上世纪80年代的金融改革推动形成了美国以消费为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同时,美元地位的加强又使得美国能够占用别国的储蓄来支撑国内的消费和投资,进而从80年代开始形成了美国贸易逆差不断扩大、其他国家贸易顺差不断扩大的全球经济失衡局面。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2000年后美国资产泡沫的形成和次贷危机的爆发?对此有很多分析视角,我从金融改革、金融创新和金融监管的关系上谈两方面。
第一,此次危机的爆发在美国国内就是没有处理好金融监管和金融创新的关系。随着金融改革的逐步完成,美国在1999年颁布了《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确立了功能监管的基本框架。可是,这个法案只是一个理念性的监管思路,对于许多金融创新产品和金融机构并没有订立明确的监管措施和监管主体。甚至为了推动金融创新,故意放松监管。例如,在2000年《商品期货现代化法案》中,将包括CDS在内的大部分场外衍生品排除在CFTC(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的监管范围之外。这样,场外衍生品成为CFTC、SEC和美联储都不监管的金融产品。再例如,对冲基金没有任何监管,而对冲基金通过石油期货和期权的交易将油价由30美元/桶炒到了去年最高的146美元/桶。对此,去年美国的几位参议员就指出,70%的商品期货合约掌握在投机者手中——这是石油泡沫的根源。
第二,此次源于美国的危机之所以能够蔓延形成全球性的金融、经济危机,其直接原因在于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垄断地位,而间接原因则在于新兴的经济强国还没有着力推动国内的金融改革,从而没有为建立多元化的国际货币体系奠定基础。我们知道,随着美元地位的加强乃至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形成垄断地位,美元的发行就必须跟上世界经济和金融发展的步伐,这要求美国的贸易逆差不断扩大,要求美国国内的经济部门——居民、企业或政府——不断扩大其自身的负债,也要求美国的金融体系围绕国内负债展开一系列金融创新。可是,这里存在一个问题——“特立芬”两难,这种两难表现为国际上对美元需求的增加与美元的信用基础之间的矛盾,即美国的居民、企业和政府是否拥有足够的偿付能力。这次危机的爆发恰恰是美国居民无力偿还其过度负债的结果。由此观之,危机的症结在于美元的垄断地位,至于2000年后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疏漏的金融监管措施只是危机爆发的催化剂。
总之,就金融监管、金融创新和金融改革的关系而言,这次危机告诉我们,一方面,通过上世纪80年代金融改革,已经拥有强大资本市场、金融创新频繁的美国需要加强金融监管,约束美元信用的滥发;另一方面,对于金融改革还没有完全展开的新兴经济强国(如中国),则需要在加快金融改革的基础上,协调好金融监管和金融创新的关系。换言之,对美国而言,现在的重点是监管和稳定;对中国而言,现在的重点是改革和发展。
对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学者和官员提出了很多建议,如要发展这种产品、发展那种市场、引进人才等等。我觉得这都重要,但都是枝叶,没有点到问题的主干。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最大的障碍是行政管制。只要放松管制,推动市场化改革,投资者、金融机构知道他们需要什么产品,需要发展什么市场,以及谁是真正需要的人才。在这方面,他们比学者和官员更为精通。